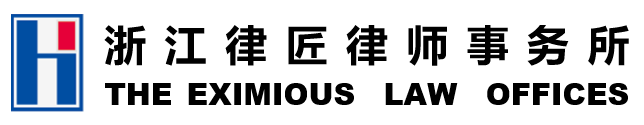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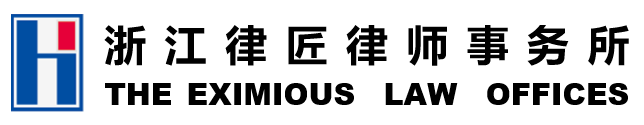

律匠学院
史正威 2019年5月16日

1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侵权案件,以笔者所在的浙江省为例,2018年交通事故数量为12768起,死亡3709人,受伤11514人(见图表)。虽然事故发生的数量逐年减少,但是绝对数量仍然很大。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浙江省2018年侵权纠纷案件的文书数量为11260件,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文书数量为9129件,占比81.07%,系侵权案件的第一大户。

▲ 摘自浙江省公安厅官网
2
由于当前大多数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未通过诉讼解决,一些不具有法律从业资格的人,俗称“黄牛”游荡在各大医院,利用当事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通过“打包”的方式赚取巨额利益。所以,反倒很少有案件认真关注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效力问题。
“法庭之上,证据为王”。在诉讼案件中,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决定性因素是事故责任的划分比例,确认责任划分比例最直接、最核心的证据则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基本上可以说,事故责任认定书决定赔偿金额。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事故责任认定书就真的无懈可击,最精确地反映事故责任的划分比例吗?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即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的效力性问题。笔者认为:
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的认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若对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当事人可在三日内到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解的依据,但是该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七十四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可见,事故当事人可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则是调解的一项依据,但是以此达成的调解协议并不具有强制力,无法通过国家力量强制执行。若调解协议未能履行,则只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行政责任的认定,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并非完全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从理论上讲,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根据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一种定性、定量的判断和确定,并以此作为事故处理中调解的依据及对违章者行政处罚的依据。
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属于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书证,且是公文书证,具有极高的证明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该司法解释明确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明力,如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看看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如何说服法官不采信事故责任认定书。
基本案情
某甲骑电动车穿过斑马线时,被某乙驾驶的机动车撞倒,导致严重受伤。
公安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某甲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某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注意减速,且遇前方车辆通过时未注意避让,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某甲、某乙的违法行为在此事故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某甲不服该认定结果,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起复核,复核结果为维持原事故认定结论。
某甲遂以某乙、某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在庭审中,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某甲损失的责任划分问题。某乙、某保险公司认可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关于责任划分的认定,认为其只应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作为某甲的代理人,笔者申请调取,并向法庭提交了事发时的视频、事发路段的照片,还原了事故原貌:事发路段双向仅有两个车道,较为狭窄,且人流较大。某甲在穿过人行横道前,短暂停靠在路边,其右手边有一辆公交车刚刚通过人行横道,减速行驶准备靠站,待公交车驶离人行横道时,某甲刚一启动电动车即被高速行驶的某乙车辆撞倒。
判决说理摘要
某乙驾车行驶在人流较大的狭窄路段,在被公交车遮挡视线,通过人行横道时,对于公交车背后是否有车辆或者行人根本无法判断,但是其依旧高速通过,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某乙违法行为的评价并不完全等同于对其过错程度的评价,除了事故责任认定书中所认定的违法行为,某乙在通过狭窄且拥堵的路段,应当也能够预见到公交车遮挡其视线,公交车背后可能有其他车辆或者行人,其未能尽到安全审慎的义务,应当减速而未减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赔偿的主要责任;另外,某甲虽然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承担自身损失的次要部分,但是其过错是通过路口时未确认安全、畅通,未能尽到安全审慎义务,并非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评价的未下车推行穿越机动车道。本案中,即使某甲下车推行,事故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依然会导致损害后果。因此,某甲未下车推行并不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与损害后果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认定该过错导致事故发生。
法院裁判结果
依据视频和照片,法院认定该组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责任划分,由某乙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70%),某甲自行承担剩余损失(30%)。
由此可见,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并非不可动摇,只要有足够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同样可以改变损害后果的责任承担。最高院《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明文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通过调取提交案发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充分、有效地还原事发经过,可以有效地说服审判人员采信该组证据,作出与事故责任认定书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过错评价以及责任划分比例。 司法实践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查阅案卷,寻找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程序问题,进而否认其效力。例如,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公安机关仍未终止一方当事人的复核申请,并作出复核认定,显然这样的复核结果就存在严重的程序缺陷。